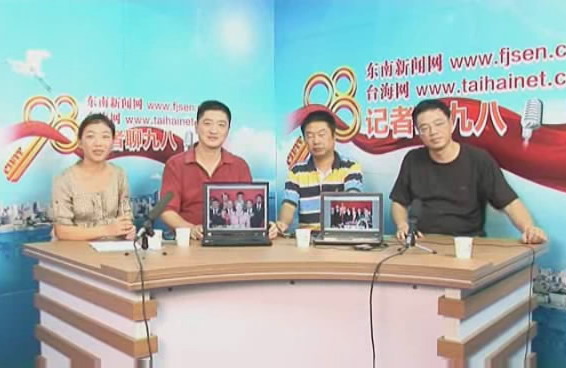兩篇評(píng)論寫作的經(jīng)過
我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談到,,前期的朱丹紅評(píng)論,,包括這兩篇評(píng)論,都是在值夜班時(shí)寫的,。那個(gè)時(shí)候是我一個(gè)人值夜班,。打夜班,,晝夜顛倒,會(huì)影響休息,,這我知道,,但是打夜班也有好處:一是審閱大量的稿件,這就給了我接觸實(shí)際的機(jī)會(huì),;二是有大量的剩余時(shí)間可以利用,。夜班從晚上7點(diǎn)半開始,一般要到凌晨二點(diǎn)結(jié)束(有時(shí)要到四五點(diǎn)鐘),,中間有五六個(gè)鐘頭可以利用,。這個(gè)時(shí)間,夜深人靜,,沒有干擾,,最有利于伏案寫作。我的習(xí)慣是,,白天看稿,,發(fā)現(xiàn)好的典型,需要配合評(píng)論,,就先構(gòu)思一下評(píng)論的大概框架,,到了晚上把版面安排好,便開始寫作,。這兩篇評(píng)論也是這樣,,白天先把題目想好,,把幾個(gè)邏輯關(guān)系弄清楚,然后利用晚上時(shí)間來寫,。因?yàn)槲覍懽直容^草,,直接拿到工廠排字,工人看不清楚,,所以就請(qǐng)辦公室負(fù)責(zé)劃版的謝文英同志幫助抄寫,。文英原來搞譯電工作,鋼筆字寫得很好,,一個(gè)是一個(gè),,很工整,而且抄寫速度也很快,。他抄好我再看一遍,,把錯(cuò)漏不當(dāng)之處改一下,就送到工廠發(fā)排,。這兩篇評(píng)論也是謝文英幫我抄寫的,,我很感謝他。現(xiàn)在,,他人雖然走了,,但當(dāng)年抄稿時(shí)那種麻利的情景依然留在我的記憶中。
我寫文章喜歡反反復(fù)復(fù)地修改,,但這兩次都沒有作大的改動(dòng),,更沒有返工,而是一氣呵成,。這是為什么呢,?這與兩篇典型報(bào)道寫得好,為評(píng)論寫作提供了新的意境有很大關(guān)系,。記者翁其華和報(bào)道組采寫的《新愚公——共產(chǎn)黨員檀積蒲》一文,,不僅生動(dòng)詳實(shí)地介紹了主人公帶頭開發(fā)荒山的先進(jìn)事跡,,而且深入地挖掘他們的先進(jìn)思想,,展現(xiàn)了他們高尚的精神境界。比如通訊中記述的檀積蒲上山前與妻子鄢英英的對(duì)話就很精彩:
鄢:“過去我跟著你長年跑大山,,住茅屋,,啃野菜,我沒說過半句怨言,。如今熬出頭了,,住上新瓦房,好不容易過了這幾年的安適生活,,怎舍得走開呢,?”
檀:“英英,,你可曾想到,過去是誰逼著我們上山住茅屋,,如今是誰使我們翻身住新房,?如今再上山、再去住茅屋又是為了什么呢,?”
鄢:“這還不明白,,過去是反動(dòng)派地主逼著我們上山住茅屋;沒有共產(chǎn)黨,,我們一輩子也翻不過身,,住不上新房。如今再上山當(dāng)然跟過去不同,。你不是常說是為了社會(huì)主義嘛,!”
檀:“對(duì)呀!現(xiàn)在上山是為了建設(shè)社會(huì)主義,,將來能住上比這還要好的新樓房,,那就搬家吧!”
在這段對(duì)話中,,檀積蒲和妻子鄢英英用自己的語言,,講出了一個(gè)深刻的哲理,這就是我們?cè)谟^察艱苦奮斗與人民生活的關(guān)系時(shí),,既要把它與昨天的封建壓迫區(qū)別開來,,又要與明天的幸福生活聯(lián)系起來。這段對(duì)話講的這幾個(gè)關(guān)系非常好,,我的文章實(shí)際上是對(duì)他們的談話作了一個(gè)解讀,。由于主題明確,邏輯關(guān)系清楚,,所以寫起來就很順手,。記者王文鏗、通訊員黃金山等人采寫的《楮林山上不老松》,,與《新愚公──共產(chǎn)黨員檀積蒲》有異曲同工之妙,。這篇通訊在介紹共產(chǎn)黨員黃仁盛帶頭開發(fā)荒山的事跡中,也有一段精彩的問答:
問:“仁盛,,你快60了,,不說種桐種杉,就是栽茶,,收成也得幾年,,你這是何苦?”
答:“前人種樹,,后人乘涼,,有何不好,?”
問:“仁盛,我真不曉得你打的什么算盤,,你想當(dāng)官,,年紀(jì)太老,又缺文化,;圖發(fā)財(cái),,你又沒子沒孫,何必這樣活受苦,?”
答:“你說,,過去許多革命戰(zhàn)士和敵人打仗,流了血,,拚了命,,他們圖的是什么,打的是什么算盤,?”
簡單的兩問兩答,,把黃仁盛革命樂觀主義的寬廣胸懷合盤托出,讓人們無不口服心服,。抓住這個(gè)話題做文章,,就把艱苦奮斗精神推到了一個(gè)新的境界。
通過兩篇評(píng)論的寫作,,我對(duì)先進(jìn)典型報(bào)道與評(píng)論,、記者與編輯的關(guān)系有了進(jìn)一步的認(rèn)識(shí),這就是:一篇成功的人物通訊,,不僅可以以其本身的感染力影響讀者,,而且還能催生意料不到的評(píng)論佳作,甚至對(duì)評(píng)論的成功與否起著決定作用,。事情很明顯,,假如沒有記者采寫的這兩篇好通訊,我的評(píng)論是絕對(duì)寫不出的,,就是寫出來,,也不可能是成功之作。
當(dāng)然,,也有這樣的時(shí)候,,典型寫得很好,,而評(píng)論沒有寫好,。我也有這樣的教訓(xùn),比如配合《八女跨海征服荒島》寫的《什么是幸?!芬晃?,人民日?qǐng)?bào)就沒有轉(zhuǎn)載,,而是自己另寫了一篇題為《敢于斗爭》的短文,配合典型報(bào)道發(fā)表了,。這說明我沒有抓準(zhǔn),。但是,為配合三個(gè)大典型寫的三篇評(píng)論,,有兩篇能為人民日?qǐng)?bào)轉(zhuǎn)載,,我已經(jīng)很知足了。

 |
|
|